“摄影不是拍照”的理论命题,早有所闻,近年更是被提到175年摄影发展与摄影艺术发展规律的高度,且断定二者竟有“天壤之别”。对此心生疑窦,遂略做些小考。
摄影术是欧洲人发明的,但摄影一词并非外来词汇。摄影术是法国人1839年发布的,至少在1944年,广东学者邹伯奇就写下光学著作《摄影之器记》。“摄影”与“拍照”都是动宾结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摄”与“拍”是获取过程,“影”和“照”是结果。《辞海》里对于“摄影”一词的界定是“用照相机或电影摄影机等摄取影像的过程。”对于“照相”的界定是“用照相机获取影像的过程。”二者的区别只是“摄影”包括电影摄影而已。作为动词,“摄影”与“拍照”也都是按快门,取得“影”和“相”的过程。
现代的影楼依照往日习惯仍旧通称“照相馆”,但影楼里主机拍照者称“人像摄影师”,并没有“人像拍照师”一说。某一摄影名家外出,别人也会说他“摄影去了”,不会说他“拍照去了”。可见,“摄影”与“拍照”的词义和习惯说法早已约定俗成。
“摄影”与“拍照”只是说法不同,并无高下、优劣、雅俗之分。至于拍什么,如何拍,拍成什么样,就是另一回事。以“摄影与拍照差异”立论,当然并非是文字概念游戏。其主旨在于对大众摄影兴起后,图像泛滥、影像摄取的过分随意性、社会历史责任感缺失等现状的忧思,对于纪实摄影的呼唤等。但对于当下摄影态势评说有失偏颇,其论证逻辑明显错位。

人类发明摄影就为了留存现实。摄影自发明伊始便被用来记录现实,尤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种对于摄影的信任来自于镜头影像所具有的指向性,让人们相信这个对象的存在是真实的。而且这种再现具有瞬间凝结的独特性,随着时空的转换,照片可以复制而同一瞬间却不可再复制。这当然是摄影最可贵的独特性。
摄影作为科学技术手段,其本体的发展变化首先决定于器具。数码迅速改变着摄影本体,从影像载体到摄取、存储方式、后期加工、传播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影像由实体变为虚幻的存在,摄影本体迅速实现“量变遽到质变”的一个飞跃过程,摄影的应用场景范围日益广泛。
数码时代,镜头对于影像的写真性并没改变,重点是手段的变化在改变摄影本体的同时,也带来摄影审美观念的流变,改变人与图像的审美关系,大大改变了“观看的标准”和“尽收万物”感觉,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诸多关联。
数码高科技时代,由于摄影技术的高度简化、普及,摄取影像器具的多样化、微型化、智能化、高清化、一体化,如今,摄影、摄像不再仅仅属于贵族、精英阶层,而是名副其实的“大众化的玩艺”,成为高科技时代大众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情势下,政治功能的淡化和娱乐功能的泛化、摄影艺术和非艺术的界线更加模糊,技术与艺术的再度交融等等是必然的趋势。
人们在留真的同时,也热衷于唯美、梦幻的追求;留真、创意、唯美各得其所。如今是跨界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在整合,都在交叉,都在相互渗透,摄影也一样。在摄影艺术门类、题材、体裁、风格的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下,把社会纪实摄影界定为褒义的、真正的“摄影”,而把大众的摄影统统界定为贬义的、异化的“照相”,这显然有悖于摄影自身发展的规律。

摄影精英群体历来是摄影的主导人物,他们在人文纪实与自然风光、创意、唯美各领域,各显其能,英才辈出。数码影像的迅速普及,摄影手段的多元发展和社会各阶层爱好者的参与,极大地改变了摄影艺术队伍的结构。数码时代,摄影人已形成主流、精英、大众三个层面,但并没有绝对的界线,更无高下、优劣之分,而且相互交融。
社会公众摄影活动的娱乐性、休闲性、随意性、当下性,恰好体现了快速地发展的信息科技时代公众的审美需求和文化权利,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有哪一种比摄影更易于上手,更易于立竿见影,更具有难以尽言的无穷乐趣吗?肯定没有。较少行政干预和功利追求,更多的是个人需求、个人行为。
他们乐于为亲人写真,为自己的行旅留念,或寄情山水,或追踪珍禽,或迷恋佳卉,或随手街拍;三朋四友参与沙龙活动,数十人面对同一良辰美景、同一名模佳丽,频频揿动快门,即使结果大同小异,他们也能从中领略到“自我实现”的乐趣。众多以风光花卉为题材的摄影比赛,也仅仅是群众性商业性文化活动,无可厚非,也不有几率会成为新闻纪实“摄影”的畔脚石。
其实,各类摄影题材有其隔离性也有其相接姓。有人说“摄影”要有文化,要用心。其实,即使是三岁的孩子镜头对准哪里,何时快门,也是有所寻思,有所选择的。快门人人会按,至于心的深浅,看的高低,那是另一回事。天津摄影家莫毅有过把照相机背在背后,骑在车上用快门线随意按的尝试,算是别出心裁,但这也是为了回应有人指责他镜头下的世态冷漠。
庞大的大众摄影队伍,各有所好,追求不一,其中的若干佼佼者也可能“玩”出一些“绝活”。事实上在新闻、纪实领域已有众多业余高手,有许多现场性极强的突发新闻,往往都是出于业余摄影人之手,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比如,英年早逝的当代著名摄影家侯登科,只能算是体制外的、业余的。他的大型黑白摄影画册《麦客》堪称当代纪实摄影的经典之作,也是当代中国摄影文化发展高度的一个标志。无论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或是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对纪实美学潜力的发掘,文本的范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极致。
再说,广东企业摄影家刘远,师出无门,为旅游而摄影,也为摄影而旅游,边走边照,信手拈来,但泛而不滥,不乏佳作。何以区分他哪一次按快门是“摄影”,哪一次是“拍照”呢?
数码时代,新闻纪实摄影的大趋势并非堪忧,而是可喜。新人辈出,佳作累累,在国际摄影界也崭露头角。对于新闻纪实的社会文献价值已为慢慢的变多的业余摄影人所看重。武汉有一个“板眼影会”就是以城市纪实为旨归,队伍逐步扩大,各显身手,且多有佳作。
大众摄影文化慢慢的变成了注重导向的主流摄影和追求历史深度的精英摄影的补充,跟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以寻求消遣、快乐为目的的“快乐摄影”一定会更加活跃。没理由把“大众”、“快乐”摄影统统贬之为低俗的“照相”。再说浩大的大众摄影队伍的作为,也并不是人们估量、评价整体摄影态势的标准。
摄影的审美与教化功能相辅相成。就社会历史发展的需求而言,提供思想和对现实真实认识的新闻、纪实摄影毕竟还是摄影文化的主体,既呼唤变革,也为历史存照。体制内的摄影人更注重政治性、新闻性和或重大或有趣的事件,或生活场景的的实录,注重社会效益。在追梦时代,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摄影纪实大有可为,但这只是摄影功能的一方面。以写意、创意、唯美、造美为旨归的自然风光、静物、超现实摄影等,或给人以启迪、遐想,或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起到陶情怡兴、美化生活、潜移默化的作用。
题材重要,但不是评定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倡导新闻纪实摄影的主体地位,强调摄影的政治功能,不需要以对其它题材、手法的贬抑为前提,没有必要重走“题材决定论”老路。就当今的新闻纪实而言,也只有从全球一体化的宏观背景去思考,把握现实,对纷繁的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的、人文学的审视,才有可能突破表面的纪录,为现实和历史留下真实精彩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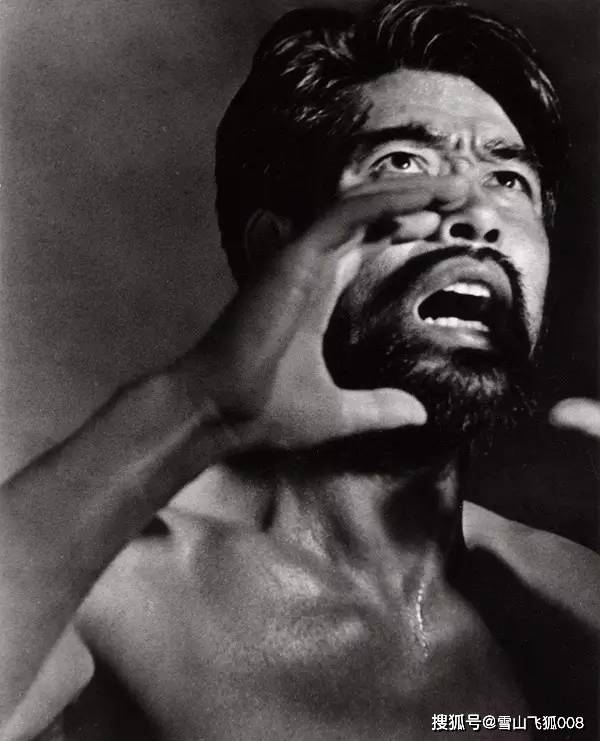
当下,大众摄影文化的发展形态趋势蔚为大观,和官方、精英、商业摄影文化形成博弈共存的共同体。各种摄影题材、艺术风格、艺术类型,各种创作方法、各类群体多元共存的格局已形成,各种艺术主张都不乏施展的空间,其间,主流、大众都有精英突显或者易位。
数码给摄影人带来无限的自由空间,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手机摄影显示的巨大魅力,令人眼花缭乱。数码摄影时代的摄影理论人,理应有理性、超前的思考,探究应对的策略。至少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强化主体意识;二是坚守“中国特色”。
“人是自身的最后目的”。自我意识不是唯我主义,而是基于“类”意识的觉醒。数字技术再强大、再万能,毕竟只是手段;数码摄影无论多么神奇,多么势不可挡,也毕竟只是人类的工具。人是数字的主人,另一方面又是自己的主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把握自己的命运,认识并掌控一定的自然规律。一切艺术创作的出发点都源于自我,源于对客观现实的自我感受。
高科技并未消蚀人的主体性地位,正确地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仍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就艺术创作而言,手段愈简单,创造和创新愈艰难。数码摄影凭借的是高科技,没有门槛,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意识、创造能力更重要。近年来,纪实摄影的发展势头很旺,佳作累累,但对于题材社会价值的重视远胜于对艺术创新和艺术个性的探究和思考。
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人面对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回答,是中国文艺之魂,也是摄影人的根基。

摄影原本就年轻,摄影理论更是滞后,国内的摄影学理建设和教学起步甚晚,西方摄影文论的引进和解读,对于中国摄影理论自身的建设起到引领作用,但是,西方的艺术理论只能是以西方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思想旨趣和艺术视野为基础的。西方的理性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理性心性化、内在化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艺术实践。
比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给了我们众多理性给养。但她毕竟是处在“前数码时代”,她的思考是从零零散散的摄影作品开始,大量列举的都是美国摄影师的作品,对于摄影的审视和追问只能立足于她所熟知的对象和视觉经验,这就难免有所局限。
就其才华横溢、旁征博引的文风而言,时有闪光的亮点,但失之严谨,前后论述难免有所抵牾。有人称之为“一份有限的观察”,是合乎情理的。数码时代,《论摄影》依然有其理论价值,但没有必要奉为不可逾越的“摄影界的《圣经》”,我们更需要的是更理性地、更自主地面对中国当今的摄影实践。
WPP(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简称“荷赛”)、国际新闻影展影赛的评价标准,国际市场的标价等等,值得研究、参照,但这只是我们走向国际的桥梁而不是终极目标。对于中国摄影家而言,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精神”,以自己的风格、艺术特色,丰富、推进国际摄影发展的历程,而不是亦步亦趋。
近年来,在荷赛中,中国摄影家屡有入选获奖。方谦华的《中国万州自然保护区内濒临灭绝的植物》、李洁军的《战争摄影图标系列》、区志航的《俯卧撑》、樊尚珍的《形影随行》等先后入选、获奖,颇出乎意料,从中不难看到国际新闻摄影观的变化,也代表着中国新闻摄影对于国际新闻摄影观念的影响。往日老是我们揣摩别人的心态,现如今他们也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相看。
对于自然风光摄影早有众多责难:诸如太多、太滥、一窝蜂、非人文等等,但摄影大众对这些论调似乎连耳边风都算不上。专家的指点、责难和公众乐此不疲的“一窝蜂”形成巨大反差。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也值得理论家深思。

西方的艺术摄影始于人物,而东方则始于风光。神州大地,山水风光、禽鸟花卉题材的摄影长盛不衰。这绝不是偶然的。理论家是不是应该换换思路,从山水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精华的角度,重新审视。在面临环境污染、城市喧嚣、人心浮躁的日子,回归自然,拥抱自然,似乎有更加的合理性。至于滥和俗,千篇一律,又当别论。
“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反映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我们送给柯达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得到的一天。”
这是刘半农先生84年前在《光社年鉴》第二集序言里写的。这话说得多好,听起来十分亲切,好像就是专为说给今天中国的摄影人听的!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形成和彰扬摄影艺术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息,是要求我们存心、而且诚心去做的。

